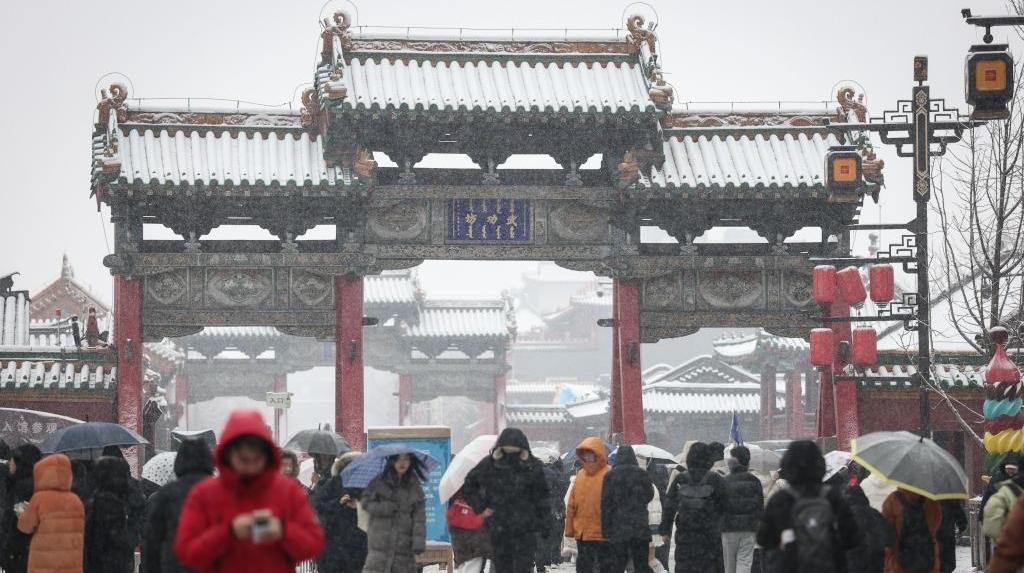田野里的知识桥梁——探访行走在乡间的大学教授系列报道之二
| 2024-05-28 09:25:36 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
东南网5月28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潘贤强 储白珊 蒋丰蔓) “没有树挺拔,没有花香,但菌草能变出山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说。20世纪80年代的福建,期待致富的群众砍树种菇,菌林矛盾突出。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在宁夏,有一群福建人被亲切唤作“宁夏菇爷”,林占熺是其中一位。闽宁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大不相同,用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难度可想而知。林占熺指导村民建半地下室菇棚、利用废弃的窑洞栽培食用菌。他经常住在菇棚里,以便夜间起来检查温度变化。半年后,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孢蘑菇等食用菌取得成功,参加食用菌生产的示范农户当年收入翻了一番多。小小一株菌草跨越山海,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续写“点草成金”的绿色奇迹。 知识的桥梁横跨“象牙塔”与广袤田野之间。行走其间的教授们,如何将理论的深邃与实践的宽广进行联结?如何为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搭建起坚实的通途?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它给乡村、社会以及大学带来怎样的变化? 乡村焕新而不止于焕新 永泰县丹云乡,生态环境好,森林资源丰富。几年前,这里和很多偏远山村一样有些萧条。现如今,因为中药材的种植,荒山变良田,产业振兴,民宿开业,丹云焕新了。 与农民打交道久了,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正高级实验师范世明时常会对这样一个现实感到不甘:为什么外地的一些中药卖得贵,而有些道地的福建中药卖不上价?“种植规模不够大,市场体量不够,缺乏很好的产业发展。”范世明希望知识能助力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 退役军人叶子渊是范世明在丹云乡结交已久、志同道合的伙伴。2016年,叶子渊来到福建中医药大学寻求高校专家技术协作,两人结识。 叶子渊说,自己对农业有着特殊的情感,想干点什么,但找不着路子。 在跟随叶子渊考察的过程中,范世明在丹云乡赤岸村无意间看见三叶青。彼时,当地政府也有引进项目的意愿,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开展三叶青种植。自此,拉开了丹云乡村焕新的序幕。 2017年9月,叶子渊创立福建天叶中草药开发有限公司,规划种植中草药三叶青和黄精5000亩,林下种植中药材2700亩,集中药材种植、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派出教授团队,进行技术指导与合作。 范世明将他的科研成果“闽选一号”三叶青带进丹云乡,从三叶青种植的品种选择、地块选择、育苗方法、生长期管理及后期管护等各环节,指导叶子渊和当地农户。 在这个合作带动下,丹云乡的发展思路开始明晰——打造“中草药种植之乡”。乡里成立了中草药种植联合基地,三叶青、多花黄精、野生灵芝、金线莲、铁皮石斛和七叶一枝花等名贵草药陆续在乡里种了起来。 2022年8月,丹云乡对位于前洋村行将倒塌的旧影剧院进行修缮改造和活化利用,将其打造成集展览展示、制作体验、药材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中草药文化研学中心。识百草、闻药香、品药膳,到访的游客可以多方位感受中草药文化的魅力。 “他们的企业每天稳定有20多人上工,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所学知识能应用于一个产业,我感觉很踏实。”如今,在丹云乡,悠悠草药香,“荒山”变“靠山”,这是范世明非常乐见的景象。 丹云乡办起了中草药文化展示厅和研学中心,成为学生实践基地。跳出乡村看乡村,教授们发现,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发展,还有生态转型、城乡融合,而这些还会让乡村发展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新时代的乡间是什么?采访中,有教授说,请不要停留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到农村中送科技下乡的观点。将理论的深邃与实践的宽广进行联结,不只是科技下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开始整合起来了。 在他们的眼里,乡村是一棵审美树,它具有美学功能、生态功能。 陈子劲,已到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7年了。他是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美育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社会美育助力乡村在地文化复兴”问题。他说,他想做的是通过专业知识弥补城乡的文化差距。 陈子劲告诉记者,他是基于学术需求而到乡村来的,有情怀可以,但情怀在下乡过程中要生成一种信念——对自己专业的信念,并且转化为一种精神的力量。 2019年,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在前汾溪村建成,孵化了“乡野艺校”公益行动品牌。于是,在这个小学仅开设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的村庄里,陈子劲和学生为孩子们开设了乡村美育课堂。 菜地、小溪、田野……“四处充满美,四处都有价值!”上课的孩子兴奋地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景色在美育课堂上重新被认识。 美育的对象同样拓展到全体村民。前汾溪村有一个遗弃了70多年的“三月三”传统节日。师生们将它重塑为创意文旅项目,并以此为起点,开展“节日快乐”社会美育项目,将节日知识变成乡野艺校课程的一部分。 这样的活动深深吸引着在地的村民——他们既当策划者,又做执行者。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家园,沉默的农夫转变为民间手艺家,害羞的村妇大胆走上走秀舞台……如今,在许多村民身上,都能看到“乡村美育”留下的印记。 “因为稀缺,艺术让人有距离感,但这种稀缺实际上是因为一种‘信息差’。”陈子劲坚信,“知识生产是为了传播,而不是把知识本身变成一个稀缺品。” 转型让乡与城“有别无差” 不止于焕新,那又是什么? 西南大学教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给出的答案是,当今中国正经历时代大转型:一是城乡转型,二是生态转型。从社会变迁来说,其实就是从乡土中国转向今天的城乡中国。有的村空心化,村中只剩老人和孩子,但像前汾溪村、龙潭村、四坪村又来了很多新村民。 来了新村民,出现了新鲜的事物。这些新村民就包括下乡的教授、学者、艺术家、文创爱好者,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屏南,新村民已有好几百人。 陈子劲成为前汾溪村的新村民。他把乡村看作是“社区”,反对用二元的眼光看待城乡之间的关系。他说,他所做的是通过立足于社区自身根脉,以高维度文明为需求,展开与未来发展相吻合的建设,以求形成乡村社区高质量、可持续的生态型发展模式。 村民的生活非常简单和朴素。陈子劲带着学生设计了一个叫作“今晚吃什么”的情景式田野调研,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找人聊天,从闲聊中获取村民的美食记忆和美食期盼,了解族谱村史,和村民一起回忆前汾溪村的变迁,激发村民对村落未来发展的热情。 陈子劲认为,艺术家参与乡村振兴不是去消费乡村文化,应该是通过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生成新的生产力,建设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共同开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并构建在地村民美好生活图景的关系路径,尊重并建设性保护好村落传统形制的物理样貌,尊重并活化保护好在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尊重并发展性保护好乡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陈子劲说。 在前汾溪村,“三月三”传统游龙节日变成了创意文旅项目。在此基础上,陈子劲和学生还鼓励村民开垦已被废弃十几年的农田,共同参与生态农业建设,一起打造生态种植和养殖体系。 为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搭建起坚实的通途。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人出去打工,农村出现空心化,只有“流人”,没有“来人”。现在变了,乡土中国正在转向城乡融合的中国,工业文明正在转向生态文明,传统经济正在转向数字经济。 城乡融合,必然会有人“流”出去,也有人“流”回来,还有新村民“流”进来。 这种“社会之变”造就了新时代乡村价值的多元。比如,农田不再只有单一的生产功能,它已经释放出疗愈功能、美学功能和生态功能。 乡村的未来正在到来。从乡—城一体的角度看,这些“空心村”是充满人烟的,只是这些居民的一部分时间在村里,另一部分时间在城市。 “推动这种生态的转型,是因为中国原来是‘乡土中国’,但现在越来越变成‘城乡中国’了。今天的屏南,它不只是乡土屏南,它有1/3的人在外面工作,1/3的人可能在县城,1/3的人在村子里。”潘家恩说。 城与乡,泾渭不再分明。乡村有互联网,有先进的物流,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生产知识,都可以将知识变成商业化的东西。教授们说,在这个物理空间里,它是适合于现代人的一种生活。 “现在的乡村,手机是新农具、数据是新农资、直播是新农活。”有教授打趣道。 城乡融合的社会,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唐任伍曾有这样的描述:乡村在风貌上保持农村味,在功能上紧跟都市风,是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美丽田园、美丽庭院、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相叠加的新形态。 这种“有别无差”,也许就是乡与城的新型关系。 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也曾空心化,常住人口只有数十人。 潘国老,一位对农业几近失望的乡贤,因一群教授留在了村里,还种了一大片田。 2020年,屏南县政府与国内多所高校联合成立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落地四坪村。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任院长,潘家恩任执行院长。 当年年底,研究院召集四坪村乡贤,开了一场“爱故乡座谈会”。看到这么多专家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古村落忙前忙后,潘国老心生好奇,受邀参加。在座谈会上,他听到了很多新概念:生态农业、市民下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新农人”。 转型让乡与城“有别无差”,同时,也让当地的农民视野更加开阔,老农人成了“新农人”。 “不是回来开荒就叫新农人,应当有新的视野和思维,同时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潘国老决定再拼一把。在研究院的指导下,他发起成立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把眼睛瞄向村里那1000多亩撂荒耕地。 四坪村的耕地几乎是分散破碎的山垄田,毫无成本优势。“换一种方式种粮。”研究院生态农业与生态文明转型中心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教授王松良为潘国老带来了关于生态农业的启蒙。 生物农药、有机肥、绿肥还田养地、稻田养鱼、鸡粪发酵回田作饲料、杂交稻混种有色稻……有教授们做靠山,他相信“用养结合”能让这片土地更加健康可持续。 接地气的不仅有人还有知识 当学问深扎于大地,大学里的人将经历怎样的变革?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冬亮自从2001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就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在“三农”问题研究上不断耕耘,走村入户,翻资料、查数据、问情况、看变化,形成了近亿字的一手研究资料,从更广泛的田野研究中扩展自己的学术研究视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2011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从人类学者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科,朱冬亮的学科背景让他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人类学的定性研究、田野参与观察等训练。 “厦大马院的教学研究走向乡野,逐渐形成了一个特色,这种特色也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关注。”他说,“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只是采用的方法是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 10多年来,朱冬亮有了更多的体会:“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位实证主义学者,进行实证调查正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本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需要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开展基层调研是将两者结合的重要方式。” “西方人类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不间断文明、文化丰富、社会复杂的情况?许多学者的答案是怀疑甚至否定的。”朱冬亮说,“马克思主义学科要具备学术生命力必须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我们需要接触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还必须与其他学科交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要真正深入田野研究现实问题,就必然和别的学科研究交融交汇在一起。”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实证调查和不同学科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老师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做思政教育,学术研究也不停留在经验式的研究和对经典的解读,而是深入中国农村中去发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对于变革,福建农林大学农业生态学教授王松良则用他课堂的两次“自我革新”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起,王松良就在福建农林大学教授生态农业,囿于种种因素,下乡次数寥寥。2000年,从荷兰访学归来的他萌生了课程改革的念头,“生态农业若继续纸上谈兵,学生学不到东西”。 王松良将其执教《农业生态学》课程当中的实践课占比从18%提升到36%,将学生带出教室,去超市调查农产品农残成分,去农场了解新型经营体制。 2019年,王松良启动“草根教授”计划。借助与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合作,他再次将《农业生态学》课程进行改革,把在黑板上讲的生态农业放到乡下去实践,创建“参与式”和“研讨式”课程教学体系,并将更多学生带往乡间的生态农业基地。 王松良说:“我们不要老是讲学术的语言,要学会跟农民打交道,学会怎么跟村干部聊天。” “把学生带到田间地头,从与新老农人的实践和学习中获得经验,再回到教室和实验室里学习农业生态学知识和技术,才能培养出乡村振兴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进而为新农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及教师评价体系的革新提供活力。”王松良坚定地认为。 把乡村的淳朴与智慧带回校园,将乡村的实践经验融入教学。行走乡间的大学教授,在实现自我转变的同时,更让学生发生了思维转变。 中国科协公布2023年度科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福建浦城再生稻科技小院志愿服务队林文雄入选“最美科技志愿者”。 几十年来,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文雄一直研究再生稻。他从学生时代就跟着导师下乡。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当老师开始,林文雄就指导学生行走乡间——因为应用科学就一定要下去,水稻跟人一样,用的都是生命科学的方法论。他说:“有问题不怕,只要走下去就都是办法。” 2015年起,他的科技小院团队在建阳、浦城等地建设千亩再生稻示范片,将3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示范推广面积达1.5万多亩,示范片连续8年实现再生稻两季总产量亩超“吨粮”。 立足科技小院,这批“田秀才”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农技服务,其中再生稻技术培训4530人次。“他们既帮助广大农户增收致富,也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科技文章,真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我为他们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林文雄说。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教授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因为与农民一起去做一些探索,这些论文还能够发挥出“翻译”和“桥梁”的作用,把基层经验翻译成更多人能听得懂的,同时帮助那些想来学习的人学得到的原理,而不是照搬。 罗新丹,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生。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理念所吸引,跟随着来到永泰县搜集和整理民间文书。 罗新丹的研究涉及“传统组织模式与现代企业的嵌合方式”。记者采访当日,她从现场新整理出来的文书资料中看到了解题的希望,一下子兴奋起来。 “读懂这套文书,也许我就能弄明白这个问题了!”她说,“人类学专业做田野调查的传统,一般是以民间访谈为主。我很有必要从郑老师这里学到如何读懂民间历史资料,来解我的研究之惑。” “必须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大地来解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其中第一步就是调查——去跟老百姓打交道,去思考老百姓面对的问题。”郑振满说,学生只要去参与田野调查,整个观念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生活目标都会改变。 兴奋之余,她更深刻地理解郑振满对“训练学生接地气,从实践、日常生活去理解这个社会的机制,由此才可能有中国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坚持。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陈冬梅的成长,也与她在屏南做乡建的经历紧密相关。研二的时候,她跟老师来到屏南进行乡建实践,毕业后进入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成了一名乡建工作者。去年,她重回“象牙塔”攻读社会学博士,在更高维度上研究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陈冬梅说,在屏南的经历让她的思维转变很大。比如看见新老村民起争执,以前她只会想到组织一些活动让双方言归于好,但现在会求证更多信息,去思考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他们如何更科学地分配利益,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如何。 在广袤田野上做学问,愈发深刻地影响着师生们的思维方式与职业发展,也成为推动大学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动力。采访中,不少教授谈到,这对于研究风气的改变很有益处,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象牙塔”里边做学问。 潘家恩说,大学现在一方面已经在改变,它希望能够有更多教师去服务乡村,但同时又不只是一个去作贡献的、去扶贫的角色。 教师本身在接地气的过程中,会发现自身的知识也更加接地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不再悬在半空中,他们能够让自己的知识更有力量。 |
相关阅读:
 |
打印 | 收藏 | 发给好友 【字号 大 中 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