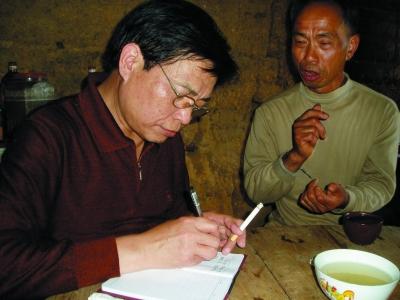风雨相伴 感恩此生有你
|
喜欢,就甭提苦和累 邱盛林
《福建日报》创刊70周年,正好我也70周岁。 人生如梦。从懵懂少年到古稀老人,算起来似乎漫长,感觉起来却很短暂。过去的事好像昨天刚发生。无论是时间老人蹒跚而行,还是回忆小子疾步如飞,当一路追逐到放得下时,万事皆休中却有一件事放不下,那就是《福建日报》的通讯员。 初识《福建日报》,是我读小学的时候,记得那时还是一张两开四版的报纸,也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张党报。让我对她产生兴趣的是,县里一位干部到我村上采访的稿子见了报。从此,我总爱到生产队长家里找唯一的一份报纸——《福建日报》来看。看着看着就做起梦来:长大后也当个给《福建日报》写稿的记者。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正在田垄里割晚稻,大队通讯员“满堂红”为我送来一份通知,同时以口相告:去公社开通讯员会。当时我很纳闷:难道公社缺通讯员,叫我去打开水、扫地?后到了会场,听了领导讲话才明白:原来给报社、电台写稿子的也叫通讯员。这回真算是与党报结上缘了。 就这样一步步从生产队长、工地报道员、公社报道组副组长走进了专吃新闻饭的县委报道组。我是1979年3月到光泽县委报道组的,1980年夏参加《福建日报》培训班的情形还在记忆中珍藏着。记得培训班结业时,报社一位副总编送给大家一句话,叫“来日方长”。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我的宿命,“来日”竟成了“一生”。尽管在40多年里有过当行政领导的机会和调县政协当科教文卫和文史办主任,但我始终没忘《福建日报》通讯员的角色,给《福建日报》写稿仍是我的第一要务。 现在还记得头次去送稿的情形:走进那栋旧编辑大楼,心里就怦怦直跳,有如丑媳妇怕见公婆。然而走入编辑部却有如回家一般。你只要把稿子送到编辑面前,尽管他们正在编辑稿子,也会很热情地放下手中的红笔,认真地看我的稿子。看完后还会耐心地评点,提出改写意见,直到稿子可用为止。说实在的,如果当初没遇上江天雄、阮荣祥等一批热心的编辑,也许早就改行了。 爱上一座山,是因为山中的几棵树,那几棵为什么会让人终生相许,又是因为山所营造的大环境。我文化水平低,只读完小学加两年半的私塾。不爱烦人,稿子发出后一般不跟电话,怕编辑反感。不爱烦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多下些笨功夫,抛开凑篇数、赚稿费等名利,不是好素材不动心,不是好主题不动笔,成文后宁可改10遍也不把难题交给编辑。但归根到底还是心里有编辑,编辑心里才会有我。 爬40多年的格子,从写好人好事、动态新闻到懂得忧国忧民抓问题,从感性到典型人物到写有理性深度的大事件、重头稿,每篇稿子的背后都有编辑力量撑着。 2006年底,我调到了县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主任岗位。这时,很多朋友为我高兴,“现在不用天天写稿子”,但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每天看《福建日报》仍然是规定课程,思维习惯也是原有的状态;关心时局,思考现实,好像没给《福建日报》写稿就若有所失,感觉对不起那些关心教导的老师和朋友。 其实,党报通讯员并不是报道组的专利,只要有那份情和爱,谁都可以干。在政协上班的4年时间里,我虽然没分工新闻宣传,但我结合政协编撰文史资料、撰写社情民意、调研报告等新闻稿件和内参,虽然数量不如以前多,但一周磨一“剑”,稿件的分量却更重,上稿率也更高。很多稿都被《福建日报》各版头条采用,每年的优秀通讯员、年度好稿都没忘了我的名字和作品。 60周年那年退休后,我见不少和我一样退休的人,有的“退了休,路上遛”,有的“没事干,学煮饭”,我则自嘲“下岗再就业”。得宣传部和报道组的抬爱,又回到了热爱的岗位——光泽县委报道组,一边带身边的同事一边采访写作。有人劝我:“吸烟有害健康,退休了就别再干那份伤脑筋的事了,趁机把烟戒了去。”我说,写稿上瘾了不能停,吸烟上瘾了也停不下来,就随它去吧!嘴上虽是这么说,实际上是心里舍不得报社那些关心、帮助过我且现在仍在关注、关心、关爱我的领导、编辑和朋友。是他们引我走上了实现人生价值之路,帮我找到了益寿延年的秘方。 做新闻真的很苦很累。没完没了地采访、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都在劳筋骨、伤脑筋中度过,人永远在路上,心永远回不了家。但我喜欢,喜欢就甭提苦和累! (作者系光泽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